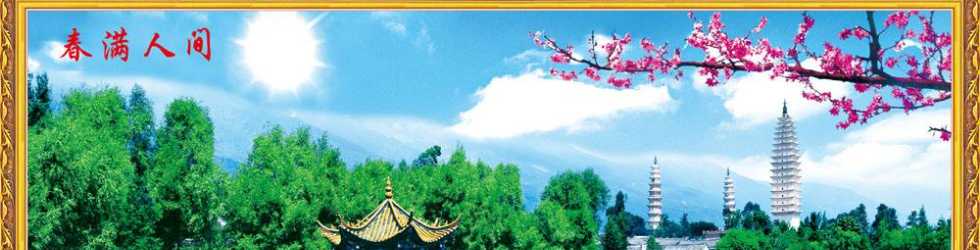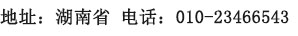安民
小时候,总是巴望着过年,可以有新衣服穿、有压岁钱拿、有鞭炮放、有花生瓜子吃,还有热热闹闹的年蒸。
年蒸,应该算是民俗文化中,特色比较鲜明的一个符号,它嵌入了百姓人家,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,盼望着自己的日子,能够“蒸蒸日上”。也正是因为有了年蒸,随着家家户户的厨房里,那热腾腾的雾气的升起,年的味道才更加的浓郁。
自从有了速冻包子,单位的年终福利,总忘不了给大伙发上一箱。有人家子女多,家里一下子有了几箱,就把年蒸的事,挤到了一边。方便是方便了,但缺少了那份年味。又近年底了,看着街头巷尾、商场内外,比平常多起来的人流,“年蒸”的场景,不由又在眼前浮现。
儿时的记忆中,只要进了腊月门,喝过腊八粥,家家户户就要准备年蒸了。
做前期准备的事,孩子们最卖力。首先,要把放在阁子上的蒸笼拿下来,连和面用的木盆和案板、装馒头用的篮子和筐,一并抬到井栏或是河边冲刷。一年不用了,上面积了不少灰,必须得好好洗一洗。然后再看看上年用的笼布、笼圈还能不能再用了,尤其是笼圈,是垫在笼屉与铁锅之间隔层,通常是用稻草扎成。往往新扎的笼圈,在沸水中煮了以后会吐黄色,头几笼馒头蒸出来,颜色就不太好看。用旧的吧,又担心哪里不规整了,笼搁在上面不容易圆气,影响年蒸时的效果,必须得过细地检查一下。
准备馅心,是件费时费神的活计,几乎都是大人们的事。一般的人家,年蒸用的馅心会有四五种,有青菜的、咸菜的、萝卜丝的、豆沙的、芝麻糖的,考究的人家还会有荠菜的、糯米饭的、马齿菜的、三丁的等等。每到这个时候,菜场这些蔬菜的出货量,总要比平时高许多。年前的这一波大众消费,总是一年中最旺的时候。
青菜、咸菜和萝卜丝馅心的制作,相对简单一些,洗净后,把青菜、咸菜剁碎,萝卜刨成丝,挤干水分,放入事先切碎的生姜葱蒜等作料,和肉丁一起下锅炒熟就可以了。现在的人学会偷懒了,怕用刀切,图省事,直接用料理机加工,殊不知料理机打出来东西太碎了,吃起来没有一点质感,味道自然差了许多。
第一次吃到豆沙的记忆,真的很深刻,那时候还很小,好像没上小学呢,父亲出差去上海,跟着去溜达了一圈。有天去了一家早餐店,刚刚出笼的豆沙包,外面看不出来,里面其实是很烫的。才一口咬下去,豆沙“吱”的冒出来,一下叮在了舌头上,吐都吐不掉。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,家里也可以做豆沙包子了。不过,豆沙的制作,要相对复杂一些,红豆要预先泡,涨开以后用石磨来磨,再用纱布吊渣,吊出来的豆沙沥干后,加入白糖、桂花、荤油等调料一起下锅熬,熬成膏状就可以了。豆沙包圆子也很好吃,特别是那种,加一块“核子油”在里面的,滑过喉咙时的感觉,美妙无比。只不过现在怕“三高”,一个个都不敢吃了。
芝麻糖,通常是孩子们的最爱。芝麻淘洗干净以后,要先下锅炒,等到芝麻香味出来的时候就快熟了,然后起锅冷却一会儿,再用碾槽将它碾碎。碾的时候还不能急,一次只能挖两三勺芝麻,多了在碾压的过程中就容易溢出来,只能一次一次地慢慢来,所谓慢工出细货,我想也不过如此。
家里有一只生铁铸的碾槽,看上去有了年头,每到中秋和过年前,就有许多街坊邻居到家里来碾芝麻。母亲一边打理着针线活,一边与邻居们拉着家常,遇上不太会弄,便会丢下手中的活计,帮人家来碾,一两个钟点很快就过去了。也有人家用石臼冲的,不过,由于每家每户所用芝麻的量都不大,也只刚刚填住了石臼的底,冲起来,还是不如碾槽来得方便。
碾碎的芝麻,拌好了糖,便装在了瓷罐里。甜的食品,总是孩子们的最爱。乘人看不见的时候,便会悄悄地去偷吃两勺。慌里慌张的,常常会将瓷罐旁边洒了一片。爷爷时常会调侃:不得了!我们家来了只大老鼠,还能将瓷罐盖子打开!每每此时,便会埋下头,不吭声,不接他的话。
馅心准备好了,就要选日子。不去扒皇历的人家,一般会选在农历的双日。日子定下以后,第一天晚上就开始准备起肥。先把面粉在盆里和好,将事先准备的老酵均匀地嵌入其中,然后在盆上面架上扁担或是其它干净的木棍,再覆上棉被。当天夜里,父亲会起来两三次,看看肥来得怎么样,也就是发酵程度如何。经验足的,会控制在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左右,要开始蒸的时候,肥来得正好。这么个时间的把控,主要还是靠经验,书本上的道理也许说得很到位,但实际操作中的拿捏,还是在各个人。
什么是白案的大师傅,那是多年的案前实践,扎扎实实地摔打出来的。发酵到家的面,在盆里膨胀开来,里面产生许多大大小小的气孔,表面撑开道道宽窄不一的裂纹。下一步的扳碱,是个技术活,更是体力活。要把碱拿捏得到位扳得均匀,寻常人家又不是饭店的白案师傅,做到实在不容易。大冬天的,父亲在扳碱时通常只穿一件棉毛衫,揉面的过程中,额头依然会渗出细微的汗珠。
碱扳好以后,笼锅水这时也烧开了。第一笼通常是将不同馅心的都做两个,看一下碱头的适应程度,也试一下火功是否能够顶上来。出笼以后,大人们通常会说上几句吉利话,那个时刻,标志着今年的年蒸,就正式开始了。
捏包子可真是件细巧活,虽不如餐馆里的厨师,做得那么精细,青菜、咸菜、萝卜丝的包子,也要捏到二十道褶左右,豆沙的还会更细,糯米饭的稍粗一些。关键是中间的那个鱼嘴,捏得不好,上笼一蒸,便咧嘴笑了开花。芝麻糖的最简单,做成馒头状就行了。其实这些手工技艺,都是平时练出了的。如果有机会,能亲自参与,多一些实践,估计你也会做得很好。
蒸的过程中,还有一个关键的人,是在灶膛烧火的。这个人不仅要掌握好火候,保证蒸笼内的气圆气足顶得恰到好处,还要兼顾出笼、点红、洗笼布和加笼锅水,基本上是从头到尾,在灶上灶下转得不歇。有好多年,家里的这个活,都是我承包的。至今还记得母亲在灶前教我的几句话:“火要空心,人要忠心,做事要专心。”是教我学会做事,也是在教我如何做人。
“年年有余”,是百姓人家最实诚的期盼。有的在年蒸的时候,还会蒸上一对鱼。那个已经磨得圆润光滑,有了多层包浆的木模,不知道是从祖上的哪一代传下来的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,拿出来洗净晾干,将面剂填进去,压出个鱼的形状,再放到笼里去蒸。出笼的时候,虽不能算是栩栩如生,倒也像模像样,得用托盘装了,端端正正地放到家里的老柜上。这一对象征着“吉庆有余”的鱼馒头,须等到正月过完了,才可以再蒸了吃。
在老街上,有些人家没有大锅灶,年蒸时,要么合在亲友家一起蒸,要么就送到街上的包子铺去蒸。每年到这个时候,有的店铺忙不过来,干脆停掉了平常的生意,专门做年蒸。需要加工的人家,自己先将馅心做好,拿到店里来排队。由于省去了在家发面、扳碱、捏包子的环节,人就轻松多了。店里的师傅,是天天和包子打交道的面把式,碱头、火候都拿捏得很准,蒸出来的包子,都是煊噗噗的,非常的喜庆。年蒸嘛,图的就是个吉利,因而送去蒸的人家也开心。
要说吃包子,其实一年到头,街边的小饭店都开着,每天都可以可以买到,但每到过年前,家家户户还是要蒸的,或许,那才是家的味道,更是过年的味道。因为是自家做的馅心,非常适合家里人的口味,当然和店里买的大路货不一样。大多数的人家,都会蒸到十几、二十几斤面。刚出笼的包子,相互之间会粘连,必须分开了,放在匾子里晾干,再装到篮子里。考究的人家,会在托盘里,垒出一个元宝状,图个吉利,谓之“招财进宝”。
年蒸的时候,孩子们最乐意做的,是“点红”。就是在馒头出笼以后,用事先做好的印戳,在不同馅心的包子上,点上不同形状的红色印记,以便区分。通常是馒头还没点好,自己的脸上、胳膊上,早已点得花里胡俏。更有看着大人在捏包子,自己也想上前参乎,结果脸上身上沾满了面粉,像戏台上化了妆的丑角,让人忍俊不禁。再一个就是忙着吃,每种馅心的包子蒸出来,都要抢着尝个鲜,最有意思的,是刚出笼的豆沙包子,看上去皮子不怎么烫,一口咬下去,里面的豆沙叮在舌头上烫,想吐又烫着了上颚,赶忙挥舞着小手,往嘴巴里面扇风,与我第一次吃到的样子,几乎一模一样。
蒸好的馒头,再回锅炕一下,让水分蒸发掉部分,这样能摆放好长时间。特别是芝麻糖馅的,炕过了再晒一晒,一个个都硬邦邦的,可以吃到来年的农忙时节。记得中学在外读书时,每逢大礼拜回来,就会带上一袋子,每天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,拿上两个放在搪瓷缸内,倒上开水,盖好闷一会,再用勺子挖着吃,那就是一顿,很香的宵夜了。
馒头蒸好以后,家里面一般都会就着灶膛内的脚火,炒花生、炒瓜子。花生和瓜子炒好了,对孩子们来说:过年,就基本上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