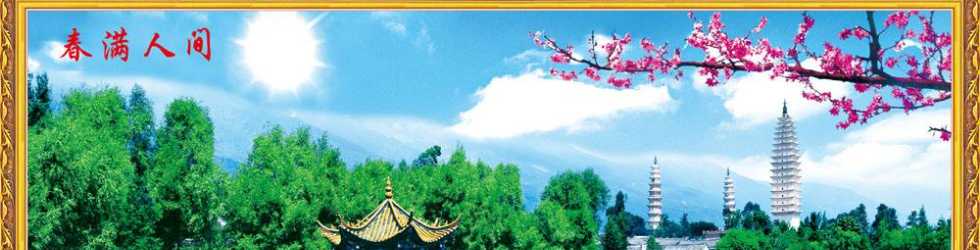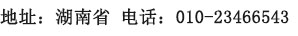近日,如果说啥事最流行,那绝对是去地里挖荠菜了。你看在地里,咱霸州人仨一群,俩一伙像寻宝一样,在低头寻找荠菜的身影多专注呀。
记得古诗里有这样一句:“春日平原荠菜花,新耕雨后落群鸦。”在我们冀中平原,荠菜和柳树一样,也是报春的使者。乍暖还寒的惊蛰节气里,人们身上的棉衣还未退去,荠菜小小的锯齿状的身影,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出现,星星点点,生长在松软的田间地头。
记得小时候,清明前后,正是地里荠菜长势喜人之际,我常常跟在母亲身后,蹦蹦跳跳一起去地里挖荠菜。母亲拎个篮子、带把铲儿,带着我走小道、越田野,寻地头村边挨个儿找去,一旦发现那掺和在绿草中的翠生生、锯齿状,带点毛儿的细茎嫩叶的荠菜。便弯腰俯身,专心致志的动手挖,随着右手铲子的起落,左手拇指与食指的拎牵,那一团软软的、絮云状的翠生生植物便攥在掌心里。
回家后,母亲择去掸去泥土,一遍遍用清水清洗荠菜,直到叶片碧青泛亮,根白耀眼,细细地切碎了,盛在瓷盆里,那馥郁的清香弥散开来,仿佛把一个春天装进了盆里。那时候家里穷,菜馅儿里只能放些大盐粒,而家里能吃到的最好的美味就是玉米面菜团子了。
我清楚的记得母亲做菜团子的过程,她的手上沾满玉米面粉,在和好的面团上揪一块放在手心里拍成薄薄的饼,放上荠菜馅子,双手合捧着慢慢抖成团,放进锅里的篦子上蒸。揭锅的那一个瞬间,热气弥散中是满屋荠菜团子的香气。母亲弓腰在热锅前,淋着水把荠菜团子一个个拾进竹箩筐里。怕烫,我不敢伸手拿,耐着性子等啊等,直到她拾起最后一个,拣不烫的一个递到我手里,我像饥饿中的小猫,双手捧着放到嘴边,就像过年的时候吃肉一样,迫不及待的吃起来。
近几年,去地里挖野菜的风气悄然升起,而且愈演愈烈。尤其是小小的荠菜因其具有明目、清凉、解热、利尿、治痢等药效,成为野菜当中的宠儿。荠菜可炒食、凉拌、作菜馅、菜羹,食用方法多样,风味独特,就是在城里的大饭店里也有它的身影。
我觉得小时候吃荠菜是一种无奈之举,但是现在不同了。现在吃荠菜不是无奈之举,而是一种时尚。人们生活好了,大鱼大肉吃得腻了,吃点野菜换换口味,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调节。更何况荠菜嚼在嘴里,不仅仅满口弥漫着的香的滋味,还有对过去那段艰苦生活的回味裹在里面,让我们这代人时刻铭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。